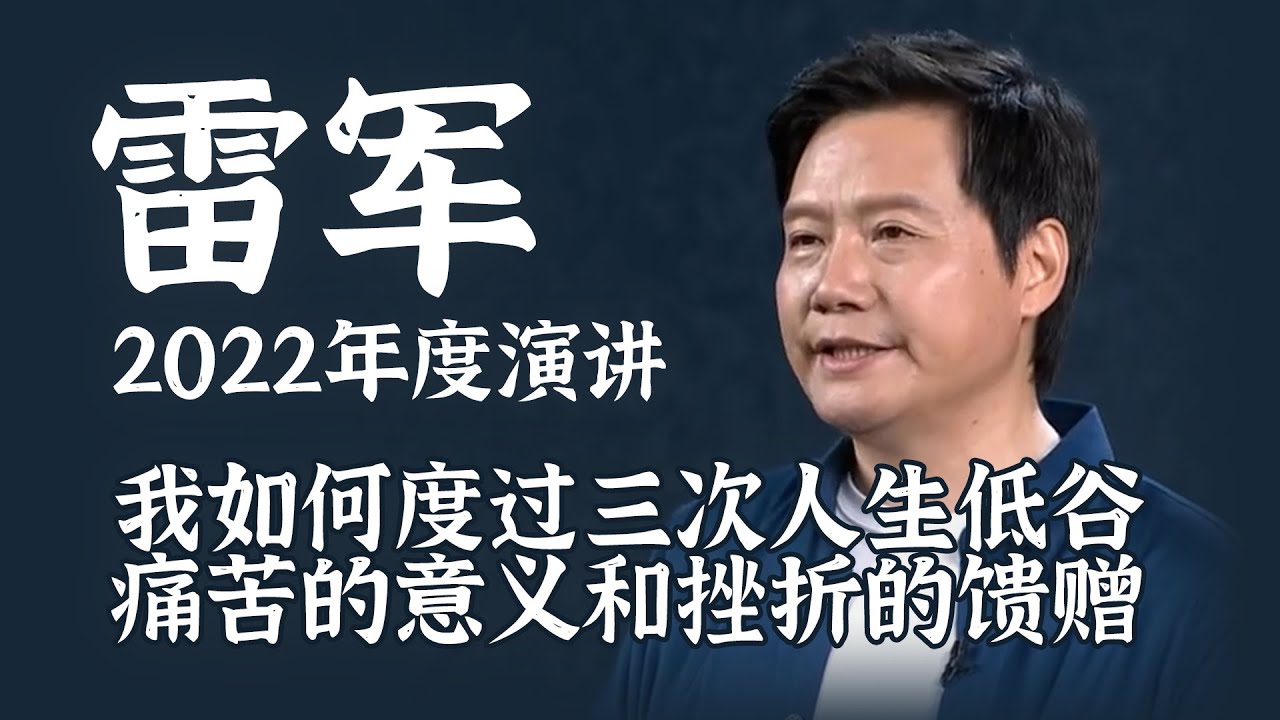宋朝的普通话是今天的河南话吗?
我们现在普遍了解一个概念,即古代存在一种类似于今天普通话的“官话”,是读书人自幼便需学习的。那么,这种官话究竟是什么样的呢?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普遍的误解。
网上常有人认为,宋朝的官话肯定是今天的河南话,因为都城开封位于河南,皇帝的口音自然成为标准。甚至有人用今天的河南话朗读宋词,声称那才是宋词的“正音”。然而,这种说法与史实相去甚远,谬误得有点离谱。
公元1039年,年仅两岁的苏东坡在四川眉州沙湖的苏家老宅蹒跚学步。然而,此后六十年的时光,他以惊人的足迹,几乎踏遍了大宋疆域的东南西北。
他的故乡眉山位于大宋西部,而他的人生轨迹却异常辽阔。向东,他曾抵达接近东海的杭州和湖州;向北,他到过与宋辽接壤的定州;向南,更是因为屡次贬谪,一路抵达天涯海角的儋州(今海南岛)。此外,他还曾在位于大宋腹地的安徽和湖北等地任职。最终,他在常州离世,葬于河南。
如此广阔的行走范围不禁引人深思:苏东坡走遍三山五岳,所到之处,他用什么语言与人交流呢?如今中国各地尚有方言差异,一千年前的宋朝,这种差异无疑更加显著。苏东坡是地道的四川人,19岁之前从未离开家乡,也未曾接触过现代传播媒介。当他去开封赶考,进士及第,步入朝堂时,他用何种语言与皇帝对答、与同僚辩论?后来,当他成为地方官,又如何主持政务、结交当地人呢?
真相究竟如何?我们不妨听一个宋朝的小故事。宋真宗时期,有两位宰相:寇准和丁谓。一日,两人在政事堂闲聊,谈及天下何地的语音最正宗。寇准来自北方,丁谓来自南方,他们的家乡话各不相同。寇准认为,天下语音最正宗的当属洛阳话——请注意,他说的并非当时的京城开封话。然而,丁谓不以为然,他说道:“四处都有方言,唯有我们读书人的口音是最正的。”
丁谓此言可谓一语道破天机。答案来了:苏东坡走遍大宋天下,他说的不是京城百姓的开封话或河南话,也不是他老家的眉山话,而是一种全天下读书人通用的、非常独特的语言——丁谓所说的“读书人的话”。
这种读书人的话究竟是怎样的呢?我们如今无从亲耳听到,也没有当时的录音留存,这确实令人感到遗憾。
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《集韵》这部字典应运而生。虽然它是在宋仁宗时期编修的,但它为每个字标注的音,并非当时北宋都城开封百姓的口音,也不是其他地方的口音,而是一种带有复古色彩的“读书音”。换句话说,《集韵》标注的正是当时读书人的口音标准。
值得一提的是,寇准认为洛阳话最正宗的说法也并非全错。因为《集韵》的前身是《广韵》,《广韵》的前身又是隋唐时期的《切韵》。有学者认为,《切韵》代表了南北朝晚期洛阳和金陵士族的语音。因此,寇准所说的洛阳话口音正宗,与《集韵》所代表的读书音,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寇准和丁谓的观点,都有其合理之处。
语同音的奇妙组合拳
汉字是方块字,统一字形相对容易,秦始皇的“书同文”便是明证。然而,在疆域辽阔、地形复杂的古代中国,要实现“语同音”——即说话一致,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。当时没有广播、电视、录音机,苏东坡在家乡时,也从未接受过朝廷推广普通话的国家政策。那么,中国人的祖先,或者说至少是其中的一小部分——读书人,他们的语音是如何实现统一的呢?
回望历史,这得益于一套奇妙的组合拳,主要有三招:编纂韵书、科举考试考诗赋、以及学堂诵读。这套组合拳在宋代得到了很好的实践。
第一招:制定语音标准——官方韵书。
标准的载体便是韵书。最初由文人自行编纂,到了宋代,更是上升为国家工程,由朝廷组织修纂《集韵》这样的韵书。
国家为何要投入巨大精力编纂韵书?这不仅仅是为了规定哪些字能够押韵,更重要的是,它为每个字给出了官方审定的读音。当来自不同地方的两位读书人在某个字的读音上产生分歧时,无需争执,因为国家规定的标准就是最终的依据。这种将韵书编纂提升为国家工程,由皇帝下诏,组织学者,并颁布刊刻的文化自觉,正是在大宋朝开始的。
第二招:推广标准——科举考试。
有了标准,如何推广?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考试。现在我们就能理解,为什么科举考试一定要考诗赋了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诗赋需要押韵,而押韵必须遵循官方韵书的标准。因此,为了通过科举考试,读书人会更加努力地学习和掌握所谓的“正音”——读书人的口音。
通过科举考试这个指挥棒,全天下的读书人,只要渴望进入仕途,便自觉地统一在这个同一个语音系统之下。所以,科举考试考诗赋,不仅仅是考察文学才能,更是考察一个未来的官员、当下的读书人,“语同音”的水平。这恰恰是进入官僚体系的“敲门砖”,因为它不仅要求你识文断字,更要求你能与皇帝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僚顺畅交流。
值得注意的是,口音是会变化的,所以并非一本《集韵》编好便万事大吉。事实上,从宋代开始,官方颁布韵书便成为一项传统,历朝历代都在不断修补完善,直到晚清1901年废除八股文(包括考诗贴诗)后,韵书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第三招:巩固和传承——学堂诵读。
你或许会问,科举考试都是笔试,不用出声,如何能统一口音?这就离不开组合拳中的第三招——学堂诵读。
我们许多人都有早读课的经历,集体朗读课文。要知道,这在中文教育中是一个独特的现象。在西方的学校里,很难听到整齐划一的朗朗读书声,他们不推崇这种方式。
汉语中有两个表示学习的词:“读书”和“念书”,它们都带有“声”的含义。这并非修辞,而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形式:将所有文字大声地念出来。鲁迅先生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描绘了他儿时在私塾的情景:先生一声“读书”,学生们便放开喉咙,人声鼎沸地朗读各种经典。
实际上,当时的学堂朗读并非仅仅是读,更带有旋律,像唱歌一样,这被称为“吟诵”。
需要说明的是,各地方言的吟诵方式并不完全相同,赵元任先生是常州人,因此他演示的是常州读书人的吟诵。不同地方、不同人,甚至不同诗文的吟诵,都会有所差异,读书人在吟诵中也有一定的自由发挥空间,并非完全按照固定的旋律来唱。
然而,正是在这种带有弹性的框架内,哪些字同音、哪些字可以押韵,都严格遵循韵书的规范。因此,正是依靠遍布中国乡村城镇的学堂,无论是官办的太学还是民间的私塾,依靠学堂里传出的朗朗读书声,中国的读书人学会了一种可以在出门做官、走遍天下时无障碍交流的共同语。这种语言在历史上被称作“官话”。
“语同音”:中华文明的强力粘合剂
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。欧洲历史上,拉丁文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。中世纪时,欧洲大学里只教授拉丁文,各国自己的民族语言(即他们的方言)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。19世纪以前,衡量一个欧洲人是否受过教育,看的不是他的母语水平,而是他的拉丁文功底。久而久之,拉丁文便成为了知识阶层和文化精英的身份象征。
世界名著《鲁滨逊漂流记》中有一个有趣的情节。鲁滨逊和他的仆人从野人手中救下一位白人。当鲁滨逊用葡萄牙语询问对方身份时,对方用拉丁文回答:“我是基督徒。”鲁滨逊是英国人,他之所以使用葡萄牙语,是因为当时葡萄牙是海上强国,他猜测荒岛上遇见的白人可能是葡萄牙人。而实际上,对方是西班牙人,并未完全听懂鲁滨逊的葡萄牙语。但他显然也认为鲁滨逊可能是欧洲人,便用欧洲通用的拉丁语进行了回应。那一刻,在远离欧洲万里之遥的南太平洋上,两个欧洲人通过共同语拉丁语实现了沟通。
所以,我们今天探讨的诗赋之学和音韵之书,在中国古代之所以如此重要,并不仅仅是出于文学艺术或闲情逸致的考量,它们更是维系一个庞大中华文明的强力粘合剂。过去,我们常强调秦始皇的“书同文”是中国文化统一的重要基础。但通过今天的探讨,我们应该认识到,中国古人还构建了另一套同样重要的粘合剂系统——那就是“语同音”。相比“书同文”,它更隐蔽、更困难,但在实际效果上也更有效。将“书同文”和“语同音”这两大粘合剂结合起来看,不得不惊叹中国文化的凝聚力是如此强大。
我们现代中国人习惯了生活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。从哈尔滨飞到三亚过冬,或从上海飞到乌鲁木齐出差,五小时的航班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。然而,这种距离放在欧洲,几乎是从东边的白俄罗斯飞到西边的葡萄牙,横跨多个国家。但在中国,这只是国内航班的正常航程。
这才是中国。它不仅空间巨大,时间延续也特别长。一个中央集权、多元一体的超级大国,竟然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时便已形成。那个时代距离我们谈论的宋仁宗时期已逾千年,甚至比宋仁宗距离今天还要遥远。而且,从宋仁宗以后,这个体系又持续了将近一千年。中间虽有分分合合,但这个体系的基本框架却始终坚固,从未完全瓦解。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奇迹。我们日复一日地生活其中,反而常常忽略了它的神奇。